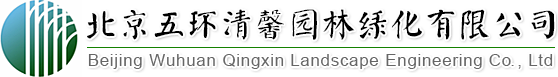創新性園林:拉維萊特公園
20世紀80年代興建的巴黎拉維萊特公園,是公認的創新性園林作品,號稱要成為21世紀的城市公園模式。這個作品在中國有很多的擁戴者,甚至它在中國的影響要大于法國,不少中國設計師在模仿它的解構主義手法。
所謂解構主義,簡單地說就是采用解析的方法,將傳統結構分解成一系列要素并重新組合,組合的原則卻不再遵循傳統的均衡與穩定,更加強調因地制宜和隨機性。建筑師屈米就是從法國傳統園林中提取出點、線、面三個體系,并進一步演變成直線和曲線的形式,疊加成拉維萊特公園的布局結構。
屈米的創新主要在于運用建筑代替傳統園林中的自然要素,構成新的點、線、面體系,認為以此構成的人工體系,結合人工化的自然,才能夠產生與城市環境相協調的城市公園。但是,這個人工性很強的公園,存在著三個方面的問題:一是造價十分昂貴;二是奇特的建筑造型與城市難以協調;三是公園更像一個游樂場,而不是讓人親近自然的場所。
那么,這樣一個公園作品為什么會在法國產生呢?這就必須了解這個公園的建設背景。20世紀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正值法國園林復興的初期。城市綠地的概念已經遭到人們的拋棄,傳統的城市公園也使人們失去了興趣。現代城市公園應該扮演什么樣的角色,如何將人們重新吸引到園林中來,是決策者和設計師普遍關注的問題。這就要求拉維萊特公園首先是一個吸引公眾眼球的設計,其次才是成為21世紀城市公園的樣板。為此,建筑師運用了自己擅長的方式,設計了一個十分張揚的公園。
實際上,對一個作品的理解,不能停留在布局、要素處理等表象上,而是要了解作品蘊含的本質性內容,從中吸取寶貴的經驗和教訓。就拉維萊特公園而言,設計師提出的有關現代城市公園的三個設計觀點很值得我們借鑒。
首先,屈米提出了“園在城中,城在園中” 的城市公園模式。力求創造一種公園與城市完全融合的結構,改變園林和城市分離的傳統。這一結構并非停留將公園的林陰道延伸到城市之中的簡單層次,而是要做到城市里面有公園的要素,公園里面有城市的格局和建筑。
其次,屈米提出了“晝夜公園”的概念。認為法國的公園只在白天開放,真正需要公園放松身心的工作人口沒有時間使用公園。為此,應借助美麗的夜景吸引公眾夜晚到公園中來。由此帶來的人氣又避免公園成為夜晚的犯罪多發地,起到改善社會治安的目的。
第三,基于城市形態的發展變化,屈米提出可塑性空間的公園設計思路。他認為,城市處于不斷變化之中,公園及其周圍土地的利用方式未來難以預料,城市的發展往往造成公園因多次改造而難以協調。而能夠隨著城市的發展而保持自身協調性的可塑性的公園結構是非常必要的。屈米采用的手法是以網格節點上的亭子作為控制點,使公園結構具有伸縮性。
其實,備受法國園林師關注的是拉維萊特公園中的十個主題園,分別是建筑師和園林師設計的,顯示出兩者截然不同的設計觀點。由園林師設計的兩個主題園是竹園和藤架園,它們基于自然和文化景觀特征,以植物為主體,著力表現獨特的園林文化內涵。竹園采取下沉式空間、擋墻、水渠和反射光、照明等設計手段,為竹子生長創造了適宜的小氣候環境條件;而混凝土和竹子這兩種材料,代表著城市和園林的活力,共同構成城市公園的理念。藤架園以葡萄園為藍本,再現了法國典型的文化景觀;夏季葡萄園中螢火蟲飛舞的情景,成為照明設計的源泉;藤本植物表現出園林空間隨時間變化而變化的特征。
上述兩個主題園成為法國當代園林里程碑式的作品,表明風景園林師擺脫了建筑師的影響,形成自身的設計語言和文化,主要體現在對自然元素的運用和對自然文化的理解方面。就園林發展史而言,闡釋人與自然的關系是永恒的主題,核心就是要表現設計師對自然和文化的理解。園林文化包括自然的能力、形態、變化的機理以及存在的必要性等等,具體闡釋園林文化的設計過程就是要加深對自然的認識,提煉自然要素并對自然語言進行重組。西方主流園林師的作品反映出他們對自然的認知以及對自然文化的把握,將自己對自然的認識融合到設計當中。
法國當代園林的發展始于20世紀70年代,至90年代初,經過20余年的努力,造就了一批有國際影響力的園林師和作品。中國風景園林的大規模建設至今也近20年了,但是為什么當代園林的發展依然未能出現質的飛躍呢?
首先存在著一個行業整體定位的問題。中國風景園林師不太注重行業特點和發展方向的研究,缺乏技術含量造成行業的門檻過低,魚龍混雜造成整個行業管理混亂和水平低下。
其次是植物材料的局限性,限制了園林的自然表現力。設計師片面追求硬質景觀的做法,造成園林匠氣十足而自然氣息喪失。離開植物、園藝的支撐,園林的發展創新有如空中樓閣。
最后還有一個公眾意識的培養問題。愛好園林的群眾基礎,是園林進一步發展的動力。人們認為,當公眾像參觀名勝古跡一樣去游覽園林時,就表明園林的時代即將到來了。公眾、決策人和設計師是相輔相成的發展基礎,園林的創新離不開各方的理解與支持。